赵禹平 - 纪录片“摆拍”理论与突破
赵禹平 - 纪录片“摆拍”理论与突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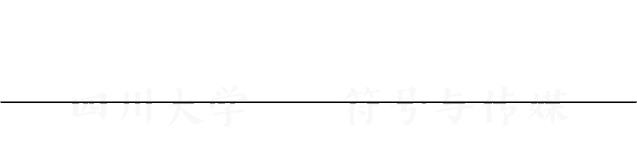

作者 | 赵禹平
摘 要
“摆拍”是纪录片故事化的必要手段。对纪录片的“摆拍”进行研究,需要借鉴对纪录片真实性的研究、对故事化纪录片的研究等,国外纪录片理论研究及实践拍摄都较早成熟。其理论中心的“摆拍”研究大致分为“创造性拍摄”“反虚构理论”“允许虚构理论”等。中国学者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对纪录片“摆拍”、虚构相关的纪实性理论开展研究,取得众多突破,与此同时,中国的纪录片拍摄也大有所为。
关键词
摆拍;虚构;纪实
0 引言
“摆拍”与纪录片的真实性息息相关,“摆拍”是纪录片故事化的必要手段。对纪录片的“摆拍”进行研究,从广义的角度而言,需要借鉴对纪录片真实性的研究,对故事化纪录片的研究,以及近些年蓬勃兴起的对纪录片虚构研究等。
相较于国内而言,国外纪录片理论研究及实践拍摄都较也成熟,较早地注意到“摆拍”、纪实、真实性等较核心议题。我国理论研究从上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进入正轨,出现了较为繁盛的局面。起初,国内研究无论从创作还是理论发展角度,都更多受到了西方纪录片创作理念和理论的影响,一路从模仿学习逐渐走上了自主研究、创新发展的道路。因此,本文采用分类别梳理法,对国内外学术界关于纪录片、报告文学构造手法以及纪录片与报告文学关系的研究成果进行文献梳理,为纪录片的“摆拍”的整体研究做铺垫。
1 国外先声
从弗拉哈迪时代开始,到繁盛的当代影视分析,国外纪录电视(电影)理论中的“摆拍”研究大致可分为六类:
(一)创造性拍摄:“摆拍”研究的诞生
20世纪20年代的“纪录片之父”弗拉哈迪也是纪录片“摆拍”的第一人。在拍摄《北方的纳努克》时,纳努克一家所居住的冰屋,因纪录片拍摄需要,在拍摄时被刻意削掉一半;又由于采光的需要,放弃在室内进行,转而在露天状态下进行纪录影片的拍摄工作。因此,起床等室内活动,实际是导演指导纳努克一家在冰天雪地里“表演”而来。这样的纪录片“摆拍”,为纪录片故事化、戏剧化的发展,以及“摆拍”的研究做足铺垫。弗拉哈迪的《我怎样拍摄〈北方的纳努克〉》也因此成为纪录片的“摆拍”教科书级文献。
20世纪30年代,约翰·格里尔逊在《纪录电影的首要原则》这篇关于纪录影片的著述当中,提出了影视所具有的教育、宣传功能需要电影工作者一起努力,担负这个引导、教育公众的社会责任。格里尔逊认为,将现实生活运用到“新的有生命的艺术形式中”①,是思想艺术的一大进步,由此还特别肯定了弗拉哈迪为纪录影片所作出的贡献。
在纪录片的教育意义立足点之外,“创造性处理”则是格里尔逊的另一著名论断,而“创造性”正体现于“摆拍”原生活,为现实事件提供一个复原的手段,即戏剧化再现。约翰·格里尔逊作为“重构”(reconstruction)的提出者和支持者,肯定了纪录片拍摄过程中“表演”(acting)的重要性。“摆拍”纪录片的拍摄方式被拍摄者反复使用,同时也受到了很多学者的质疑,而争论的焦点围绕“摆拍”是否会影响真实性的塑造、是否会导致虚构、是否应该被允许等问题进行。
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表现事物原貌”“不可交由导演导拍”“反映现实实情”等号召顺应时代需求而得到更多的提倡和支持;非虚构理论的支持者逐渐走到了历史舞台的中心,他们要求纪录电影必须真实,纪录电影必须透过双眼的观察、纪录设备的直接拍摄,直观地展现给观众。
(二)“反虚构理论”
大致在格里尔逊强调“创造性”拍摄的同时期,吉加·维尔托夫开创“电影眼睛派”(Movie eyes send),强调捕捉生活。他在论著《维尔托夫论纪录电影》中说,摄影机是可以记录“真正的现实”的,纪录电影应当打造一种不依赖演员的纯纪录式的纪录电影,而要打造纪录电影的首要任务是先打造新闻纪录片。
新闻纪录满足“直接电影”(Direct Cinema)提倡的“一般不采用事先拟定的脚本来指导拍摄的进行,反对用任何‘导演’手段对事件的自然进程进行人为的干预, 严格杜绝在影片中对事件进行事过之后的摆拍”②。维尔托夫将纪录电影的真实性放在首位。维尔托夫团队所宣扬的纪实美学,在20世纪60年代被发挥到了极致,“真实电影”的理念由维尔托夫“电影眼睛”理论影响,开始流行于欧洲,要求影片的“客观”和突发事件的真实,而真实情感和客观故事,可以以对话或访谈的节目形式展开,并不需要主观捏造、编排;换言之,这种真实情感不能被“摆拍”出来,所有用“导演”手段排除的纪录片是不符合纪录片真实性要求的。
维尔托夫和他的“电影眼睛”小组的研究以及他们的各种主张,影响着其他国家的纪录电影实践创作和理论研究,西欧“真实电影”即为一例。随着“直接电影”队伍的不断壮大,以及横跨亚欧对“真实电影”等的影响逐渐加深,维尔托夫的理论也面临着来自各界的质疑。尤其是“直接电影”那些严格杜绝摆拍、绝对不允许虚构、最大程度上减少人为介入的观点,甚至受到了来自“直接电影”团队干将们的质疑和反对。
梅索斯(Maysles)兄弟发现,“直接电影”总是以事情自身发展方式去拍摄事件,而不是有意识地强调某些有意思的片段或对话,是与“导演”“编排”完全背道而驰的拍摄方式;因而使得所拍事件充盈着不可控制性和不可预知性,这就导致被拍摄事件的不可预知与不可控,该类纪录影片就只存在有限叙述。
(三)“允许虚构理论”
20世纪60年代以后,利柯克、梅索斯兄弟和怀斯曼等人作为“直接电影”团队的得力干将,却肯定“直接电影”的真实并不与虚构完全对立的观点。他们甚至认为“直接电影”在拍摄过程中离不开主观性,而且“直接电影”的真实只能是接近真实,这种“接近真实”相对虚构而言也是较为真实。70年代中后期,梅索斯兄弟在纪录电影中不断融入现场反应、拍摄介入的手法,作品《灰色花园》代表了他们对“介入”式拍摄和指挥式拍摄的肯定。阿尔伯特·梅索斯(Albert Maysles)也在访谈节目中坦言:“我们告诉拍摄对象,我们可能会对那些感兴趣,如果他想对我们说什么,请讲。”③ 介入关系的灵活运用在摆拍直接电影反控制的同时,又避免掉入僵化拍摄套路。
利柯克强调,“旁观”美学(“Bystander” aesthetics)肯定拍摄主体的主观性。认为,拍摄纪录电影需要电影主体对生活进行细化旁观,了解事情的进展、熟悉我们生活的社会,掌握事件如何真实地发生;拍摄者只有通过“旁观”,才能真正了解社会生活的意义,事件背后的可取价值;“旁观”的方式也使得纪录电影拍摄主体、纪录电影接受主体能从不同角度对同一事件进行阐释。利柯克等一批在“直接电影”影响下成长起来的纪录电影大师,也认可纪录电影离不开主观性,纪录片的拍摄需要导演的“指导”和主观意识的介入,进行些许“摆拍”。
受“直接电影”影响的让·鲁什(Jean Rouch)把法国“真实电影”定义为电影和纪录电影之间的一种类型,兼有虚构和非虚构成分。埃里克·巴尔诺(Eric Barnouw)也提出:“直接电影”的客观性会受到摄像机的影响。克劳斯·克莱梅尔(Klaus kramer)曾指出:“为了用摄影机的贴近来达到克拉考尔所幻想的‘物质现实的复原’这样一个重要前提,现在用新的技术事实上已经完成。”④他强调,克拉考尔提出的“物质现实的复原”指摄像机的客观拍摄,而客观拍摄所不能还原的是记录材料,这就又要依赖“摆拍”。总之,“直接电影”“真实电影”需要有摆拍来还原客观物质现实,也会兼具虚构、非虚构因素。
在“直接电影”“真实电影”之后,20世纪90年代的西方纪录电影出现了“新纪录电影”(new documentary),林达·威廉姆斯作为此概念的较早提出者,不仅对纪录片和故事片做了区分,且认可纪录片的拍摄应承认虚构手段的合理性,虚构作为纪录片的创作手法之一的观点,既冲击了传统的纪录研究领域,也是一次跨越性发展。“新纪录电影”甚至认为,特定需要下的真实并不会影响纪录片的真实性,反而是在为纪录片对现实世界的真实反映做努力;这为新时期纪录片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
(四)纪录影片接受理论
20世纪晚期,与纪录电影理论同时发展的,还有与受众相关的接受理论。英国的李弗斯在《电影宣传的威力——神话还是真实》中提出了著名的“有限效果论”(limited effects theory),将从接受者角度入手的研究提上纪录电影的研究日程,有限效果论认为,大众传播并不能直接改变纪录电影接受者的认知态度;作为教育功能的纪录电影,只是在人们处理事情、做出决定之前,纪录电影会对接受者的政治、经济、文化、心理中既定的信息发挥作用,促其进行选择性接触,做出倾向性选择。
“有限效果论”提出以来,拉扎斯菲尔德《人民的选择》《个人影响》等著作中针对“传播流”,还提出了“意见领袖”“两级传播”的著名传播理论观点;霍夫兰还就纪录电影在传播者的态度和效果上进行研究。实际上,对纪录影片的接受,尤其是传播效果接受视角的接收理论,对电影研究影响颇深,与符号叙述学中的电影研究不谋而合的正是,意义的发出与接受也受到各个环节主体的影响。20世纪70年代晚期,后现代思潮涌入西方纪录理论研究,为其形式研究寻求突破口;在科技沃土的栽培下,在符号学、解构主义等的影响下,西方纪录电影理论研究冲破滞缓的现状,实现了又一次的飞跃。
(五)符号叙述理论下的纪录电影研究
20世纪形式论研究中,符号学的电影文化特征考察不容小觑。纪录电影的符号学考察由“视听”符号系统展开。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将符号学理论与电影电视研究相联系,在《神话学》著作当中,他将符号学与电视、电影、广告等中蕴含的诸多意义元素进行合并分析,通过能指、所指等概念、形式,勾勒意义生成机制,为电视电影解读提供理论基础。安伯托·艾柯(Umberto Eco)认为,“为传导某种对象或者相应概念而再现各种具体对象(如一般动物的图画)的任何视觉的程序”⑤都可以称之为符号。电视媒介的视觉效果正是以意义传达为追求,而创作者们巧妙地运用符号传递意义。艾伦·赛特(Allen Set)在《重组话语频道》提出: “对于引申意指的研究,也引导我们走出电视文本之外,并且超越了符号学的领域。”⑥
皮尔斯认为,符号的阐释过程应该包括符号、对象、解释符三个基本项的互动过程,对象虽然是有限可解的,可是解释项是无限拓展的。根据解释者的教育程度、社会背景、历史经验等,用“一物代一物”的原则,得到最妥帖的解释。无疑,视觉艺术作品是最符合解释项能够对解释者情绪、能量释放产生影响的艺术形式。
后现代的电视符号研究与社会艺术文化研究融合,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将电影符号学家麦茨聚合、组合双轴选择关系拓展到电视符号研究当中,与费克斯(Feix)的“编码—解码”研究雷同,霍尔也将电视艺术观与编码、解码流程与文本结合阐释;电视符号学的研究中心应当也是作为社会文化研究的一支,围绕文本进行编码和解码。纪录电视(电影)又是影视符号学研究的一个支流,图像、视听等媒介符号要素的研究又围绕纪录片文本的特殊性而展开;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的“拟象”研究,提出电视所折射出的虚拟社会不同于真实的生活社会的观点,与纪录片所关注的纪录电视的述真研究异曲同工。
在纪录片“摆拍”是否成为虚构作品,纪录片的真实性是否被瓦解等质疑中,学者借用叙事学,在纪录片形式研究中更近一筹,丰富了更多结构主义者的研究。20世纪90年代在西方产生的后经典叙事学注重跨学科、联系社会语境,注重读者的作用,在传统叙述学理论的基础上进行补充和修正。赛摩尔·查特曼(Seymour Chatman)的《故事与话语:小说和电影的叙事结构》对“电影叙事者”“电影叙事交流”研究而言,堪称后经典叙事学奠基之作;斯洛米斯·林蒙·凯南(Slomise Linmon Kennan)的作品《叙事小说:当代诗学》,则是对后经典叙事理论的发展。
希拉·柯伦·伯纳德(Sheila Curran Bemard)写成的《纪录片也要讲故事》,通过创作者的缜密构思,从真实的生活出发,结合各种叙事技巧,凸显故事真谛、内涵。罗比特·弗拉哈迪的案例分析著作《影像中的历史:世界纪录片精品档案》中,解释经典纪录片案例中“经典场景”配合“经典画面”和“叙述语言”,如何在叙述中满足观众的审美需求,且重点关注了纪录电影的叙述语言和叙述者。
(六)新纪录电影的“摆拍”热浪
20世纪末,“新纪录电影”在西方国家的崛起顺应了多方面的需要,后现代思潮的思想背景之中,符号学、解构主义等催生了新纪录电影的实践创作。托马斯·沃(Thomas Woll)在电影杂志《跳切》上曾指出,70年代中期的作品如《心灵与智慧》《阿提卡》等都显示70年代的新纪录电影突破了60年代真理电影的束缚,为纪录电影的新发展开辟了道路。实践发展的成熟,必然为20世纪90年代的纪录片主观性的研究发展铺设道路。
琳达·威廉姆斯(Linda Williams)在《没有记忆的镜子——真实、历史与新纪录电影》中表达对这一新纪录发展道路的肯定:“电影无法揭示事件的真实,只能表现构建竞争性真实的思想形态和意识,我们可以借助故事大师采用的叙事方法搞清事件的意义。”⑦新纪录电影,正是强调事件真实与意义升华的结合,用故事叙述方法和直观拍摄法相结合。借用威廉姆斯的分析,“新纪录电影”否定传统观察式纪录、赞同且主张纪录电影虚构、考察历史,其新纪录手段意外地获得观众的青睐。总的来说,世界记录电影整体上是一个从“摆拍”到“反摆拍”又到“摆拍”的发展过程。
2 中国纪录片“摆拍”话语的崛起
大致同时期(20世纪80年代)中国纪录片在吸收国外纪录片拍摄技巧、国外纪录片大师的拍摄理念的同时,涌现了一大批研究学者。中国学者在对纪录片“摆拍”、虚构相关的纪实性理论、技术理论上取得众多突破;在纪录片拍摄大有所为的同时,理论研究亦步亦趋。
(一)研究、学习西方的纪实理论
20世纪80年代,中国开始了纪录片的本体研究,以翻译国外研究成果为基础,研究纪录片的纪实美学、纪实方法等。随着西方纪录片理论的引入,中国纪录片的研究产生了高度的学习热情。从学者的文章中去学习格里尔逊式的创作理念,维尔托夫“电影眼睛”“直接电影”“真实电影”等相关理论。国内纪录片研究初期以来,以西方纪录片研究理论为指导、西方拍摄理念为指导的西方话语,影响众多国内研究;当然,也是理论研究初期阶段最主要的呈现方式之一。
80年代以后,对西方纪录片大师理论研究的译著,在国外文献综述部分已罗列出较多著作;纪录片研究学者单万里曾写《先驱者的足迹——纪念早期的纪录电影大师》,开专章专节对世界顶尖的摄影大师们的摄影理念和代表作品进行介绍:弗拉哈迪如何不失真地为现实服务,关于“摆拍”这一“创造性构想”,吉加·维尔托夫、尤里斯·伊文思等人的拍摄理念,罗列了西方整个纪录片历史上对真实性研究有重大成就的学者的理论。单万里从纪录片大师们那里,为纪录片的真实性探讨寻找中式批评话语而努力。
聂欣如《什么是纪录电影》、周欢《真实纪录电影的基石》、张雅欣《中外纪录片比较》、姜依文主编《生存之镜》等对西方纪录电影理论有较短概述,同时对纪录电影的“真实性”和强调还原的拍摄技巧做出论述。赖黎捷的《话语选择与理论来源:中国纪录片批评研究》从全球化语境出发,对中国纪录片批评研究中受到的西方理论研究影响进行较为缜密的罗列探讨。
在中国纪录片研究的理论著作当中,确实不乏对西方纪录片理论以及理论大师的译作和研究著作。从80年代末开始,中国学者也开始了将纪录片作为纪实文本的探讨。
(二)对纪实文本与虚构关系的探讨
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新纪录电影”理论的影响下,单万里等学者都对新纪录电影理念中纪录片的颠覆性定义、纪录片“可虚构”的拍摄方法等做出分析;中国纪录片学者也更多投入到纪录片的纪实美学、纪实方法等研究中。
纪录片作为纪实文本,虚构与否、可否虚构、如何纪实等问题受到大批学者的关注,一系列讨论纪实文本与虚构、虚拟技术、“摆拍”关系的研究结果出世。张祖坤《论纪录片纪实性与技巧性的关系》、刘腾《中国电视纪录片创作的纪实和虚拟》、陈惠茹《纪录片的纪实性和故事性》、程宗璋《论电视纪录片的纪实性和艺术性》等为代表的研究,囊括纪录片文本研究的重点内容,并在纪实叙述的问题上进行着学理性探究。
(三)多理论研究共同发展
21世纪以来,纪录片理论对纪录片本体进行叙述学、题材、主题等多方面研究,批评视角由纪录片本体研究拓展为更多元化的美学视角、文化视角,以及和国际接轨的纪录片探讨、比较。
1.符号叙述学对“摆拍”叙述的研究
赵毅衡的《广义叙述学》将广告、电影、电视等依赖媒介传达文字叙述的叙述作品纳入叙述学分析范畴,并在“用风格区分纪实虚构”的论述中,对“摆拍”在纪实风格中的影响提出见解。谭天和陈强合著的《纪录之门:纪录片制作理念与技能》围绕导演“指导”纪录片、“摆拍”叙述故事,指出纪录片的创作一定具有叙述理念,就如电影是在讲故事一般,纪录片也是由零碎的小故事叠加而成。
随着电视电影的广泛普及,最初的文学文本被电视电影新闻媒体等逐渐代替,叙述学研究则转向电视新闻、电视纪录片、电视广告。《电视叙事研究》《电视叙事理论刍议》《叙事理论与电影电视等的研究》等相关研究论文在后经典叙事学理论的视域下,结合当前社会文化、思想潮流很大程度上丰富了电视研究。
2.创作“摆拍”要素研究
20世纪末的中国“摆拍”要素研究,更多受到了“新纪录电影”的影响,在肯定纪录片虚构的同时,对纪录片“摆拍”中需要的各创作要素进行分析。纪录片创作的各要素包括拍摄者、解说者、扮演者、摄像机运用技巧、纪录片选材、纪录片分类等,研究者根据不同的着眼点进行研究。
著名纪录片编导陈光忠在《学谈新闻纪录电影》中记录了新闻纪录片的有关“选材、构思、表现方法、风格样式、音乐处理”等方面的学者经验;李则翔的《谈纪录片摄影师的素质》讨论了纪录片中纪录片拍摄者的应有素质;钟大年编著的《纪录片创作论纲》专门论述了纪录电影的拍摄方法和技巧。
3.多学科的纪实研究
与新时期的多元化社会应运而生的是多学科的纪实研究,如2010年由周文主编的《世界纪录片精品解读》和2012年出版的石屹《纪录片解读》,两本研究著作分别对每个代表人物代表作品做出美学解读。
张江华等人合著的《影视人类学概论》是代表影视研究新方向的理论总结性著作,陶涛2015年编成《影像书写历史》一书,融汇哲学、人类学、视觉艺术、符号学、叙述学等多个学科交叉分析,从多学科视角下对当下影像书写进行总结,对影视主体研究颇具借鉴意义。由石屹著的《电视纪录片:艺术手法与中外观照》,是从1958年中国纪录片的模仿时期开始成书,对当今国内纪录片、国际国内纪录片拍摄群体和纪录片的风格特征都有简要概述。
任远的《电视纪录片的界说》、赵淑萍的《中外电视纪录片的历史与现状》、吕新雨的《国外电视纪录片的发展趋势》和陈汉元的《当代中国的电视纪录片运动》,对诸如当代纪录片的叙述风格趋向、当代纪录片的导演创作、群体风格以及国际竞争下的国内外纪录片概况都做了评述。此类研究,既观照国外记录片研究成果,又注意中国纪录片与世界纪录片融合发展,弥补国内纪录电影研究发展的不足;在学习与借鉴的分析中,梳理出世界纪录片的发展脉络和基础概况。
《中国纪录片发展研究报告》则对中国当年的纪录片发展概况、主题特色、宏观格局、电影美学研究等有简要概述。中国当代学者对纪录片的分析也精彩纷呈,单万里、聂欣如、吕新雨、欧阳宏生、侯洪等的论著都对纪录电影的发展进行各方面的剖析。中国纪录片理论研究,不断寻找中国式话语并突破西方的纪实理论,创造中国纪录片文化。
注释:
①⑦单万里:《纪录电影文献》,第16页,第578页,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1年版。
②杨葳:《浅析直接电影》,《电影文学》2007年第23期。
③See the inerview of Albert Mysles by Chronicle from Austin Chronicle`s Screens feature archives on http://www.weeklywire.com.
④聂欣如:《纪录片:纪实还是游戏》,《广播电视学报》2014年第3期。
⑤[意]安伯托·艾柯:《符号学与语言哲学》,王天清译,第8页,百花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
⑥[美]罗伯特·艾伦:《重组华语频道——电视与当代批评理论》,牟岭译,第27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本文刊载于《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19年03期
编辑︱刘思薇
视觉︱欧阳言多
如果这篇论文给你带来了一点启发
-

- 太帅了!张国荣罕见证件照曝光
-
2024-11-10 17:05:06
-

- 120厘米中国最长的腿,这位女神来自大连
-
2024-11-10 17:02:51
-
- 什么是婆媳关系?
-
2024-11-10 17:00:37
-

- 未来的京沪高铁二线都经过哪里?一张图告诉你
-
2024-11-10 16:58:22
-
- 女生病娇,伤感,黑暗风句子
-
2024-11-10 16:56:07
-
- 歪阅丨天佑回归,赵佳俊豪刷十万秒榜直呼对不起,天佑阻止内斗!
-
2024-11-10 16:53:52
-

- 我与田春鸟老师
-
2024-11-10 16:51:37
-

- QQ飞车手游怎样让氮气自动喷 QQ飞车手游小喷射自动喷设置方法
-
2024-11-10 16:49:22
-
- 关于滴胶是否有毒
-
2024-11-10 16:47:08
-
- 总结必看的40本后宫流小说
-
2024-11-10 16:44:53
-

- 中国百位Rapper—C-Block
-
2024-11-09 17:56:36
-

- 石天患胃癌离世,享年72岁,曾出演《英雄本色》《最佳拍档》
-
2024-11-09 17:54:21
-

- 老城厢大夫坊,即将消失的路名
-
2024-11-09 17:52:06
-

- 揭开董欣护肤品内幕!
-
2024-11-09 17:49:51
-

- LIFORME丨如何练习瑜伽之盘腿式(简易式)
-
2024-11-09 17:47:37
-

- EVS战队进入MSI正赛,男枪表现强势有望崛起,MLXG最近也一直在练
-
2024-11-09 17:45:22
-

- 卧槽泥马是个成语,出自战国策?非也非也,实则杜撰
-
2024-11-09 17:43:07
-

- 退役军人优待证怎么用?3个方面用途,用得好就会觉得管用
-
2024-11-09 17:40:52
-

- 唐一菲,非一般的女子
-
2024-11-09 17:38:38
-
- 什么是隐形补发?
-
2024-11-09 17:36:23







 76岁退休大妈,连续30年每天一杯沙棘原浆,揭秘沙棘原浆3大谎言
76岁退休大妈,连续30年每天一杯沙棘原浆,揭秘沙棘原浆3大谎言 适合60-80岁老人代步的4种电动车,不限年龄又能上路
适合60-80岁老人代步的4种电动车,不限年龄又能上路